
救援物资托盘从运输机舱门倾泻而下,降落伞在坠落过程中砰然张开,朝着下方加沙地带饱经摧残的饥民缓缓降落。
在这片临海土地上,绝大多数居民被迫逃离家园,挤在仅剩的狭小区域。
居住在帐篷营地里的人们,每天都在为寻找食物、饮水和药品而挣扎求生。
那些承载着往日记忆的房屋、商铺和街巷已被夷为平地,即便战争结束,他们也再无家园可归。
自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以来,两年间以色列对加沙发动了现代战争史上罕见的猛烈军事打击。
整个社会正在分崩离析。
当地卫生部门数据显示,超过6.7万人丧生,相当于每34名加沙居民中就有一人遇难,无数家族谱系被拦腰斩断。
上月联合国调查委员会认定以色列对加沙巴勒斯坦人实施种族灭绝。以色列否认指控,称其目标在于消灭哈马斯并解救在袭击中被劫持的人质——该事件造成1200人死亡。
以色列与哈马斯谈判代表正在埃及就交换被扣押人员展开磋商。若达成协议,可能推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新版停火方案——此前多方调解屡屡受挫。
至今无人知晓,这片土地的未来该由谁治理,重建家园的巨额资金该由谁承担。
当下,绝大多数人光是挣扎求生已耗尽力气,无暇思考未来。
“只有战争真正结束,我们才能考虑战后生活。”前加油站员工哈姆扎·萨利姆说。他在冲突初期的猛烈空袭中失去了双腿。
残缺的躯体,崩塌的人生
战前,萨利姆与妻子和四个孩子——三子一女——住在加沙北部。五岁的女儿莉塔尔刚上幼儿园,最爱串珠编织手链。
“那时生活充满希望,感谢真主。”萨利姆回忆道。
战争改变了一切。
据萨利姆及其在袭击中受伤的父亲回忆,战争初期某次空袭击中莉塔尔附近,她右手腕以上部位被炸断。以色列军方称当时正在打击哈马斯军事设施。
三个月后,当全家逃至加沙南部时,又一轮袭击炸伤了萨利姆,最终他双膝以上部位被迫截肢。
随着加沙医疗系统崩溃,父女二人求医无门。
以色列部队多次疏散、突袭并空袭医院,指控哈马斯将其作为掩护。世卫组织数据显示,加沙36家医院中仅有不到半数维持部分功能。
战事持续导致药物短缺,癌症治疗与透析服务近乎断绝。
今年北半球春季以色列封锁所有援助通道后,饥荒开始蔓延。
八月,国际专家小组宣布加沙超50万人正经历“人为制造”的饥荒,其影响包括饥饿、急性营养不良与死亡。
专家指出营养不良与创伤会阻碍身心发育,意味着这场战争的健康阴影将笼罩整整一代人。
“疾病与死亡的威胁如影随形,孩子们每天都在与之抗争。”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加沙发言人特丝·英格拉姆表示,“这种毒性压力不仅有害,长期更可能危及生命。”
以色列官员淡化当地饥荒严重性,称正努力协助援助物资进入。政府斥责饥荒报告“纯属谎言”。
以色列军方声明仅打击军事目标并遵守国际法,指控哈马斯在人口稠密区建设军事设施——包括指挥中心、武器库和作战隧道——并在道路民宅设置诡雷。
世卫组织统计,加沙16.7万伤者中超过四分之一遭受“改变人生的重伤”,超5000人截肢。
以色列封锁边境使民众无法像叙利亚、乌克兰难民那样逃离轰炸,伤者亦难赴海外就医——医疗撤离许可极难获取。
萨利姆说莉塔尔的断肢在混乱中遗失无法再接,医院物资短缺迫使他从药房自购麻醉剂。另一次爆炸令他昏迷十天,醒来才发现双腿已失。消毒不当引发感染,出院时无药可用,只能硬扛剧痛。
九月以色列对加沙城发动新攻势,全家再次逃亡。父亲和儿子们推着轮椅,在破损的沙土路上蹒跚跋涉至加沙中部。
现暂居姐姐家的萨利姆一家衣物钱财所剩无几,连应急帐篷都没有。“我们无处可去了。”他喃喃道。
破碎的家园
联合国估算加沙近八成建筑受损或被毁。截至去年十二月,当地堆积5000万吨废墟,需105辆卡车连续清运21年。
世界银行二月评估物质损失达299亿美元——相当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年经济产出的1.8倍。
数字无法尽述失去的全部。当日常生活的坐标——买番茄的商铺、会友的咖啡馆——接连消失,过往人生也随之湮灭。
三个孩子的父亲尼达尔·伊萨曾在加沙城经营婚纱店,他与近30名亲属同住的公寓楼是生活中心。卫星影像显示,如今这里连同街角的柑橘林、肉铺和儿子常去的理发店皆成废墟。
“我最好的年华都留在这栋房子里。”32岁的伊萨说。这里见证家族所有重要时刻:新生儿降临时分发的甜点,新婚夫妇的庆典宴席,悼念逝者时的苦咖啡与椰枣。
孩子们曾在联合国运营的学校就读,家人在附近诊所就医。他的“白衣天使”婚纱店距此仅需短暂车程。
战争初期附近卡车遇袭波及店铺,他抢运出部分婚纱配饰存放家中。八月以色列轰炸居民楼时,这些最后的存货也化为乌有。尽管军方通过邻居发出预警,全家得以逃生,但家园已不复存在。以军称此次空袭针对“军事目标”。
家族成员被迫四散避难。伊萨与妻儿最终流落加沙南部,栖身于帐篷中。他渴望在不再由哈马斯统治的加沙重建生活。
“如果战争能以解决方案告终,统治体系得以改变,我会重开店门,留在故土。”他说,“最重要的是换掉那个将我们拖入毁灭的政权。”
逝去的童年
14岁的马哈茂德·阿布·沙赫马同样住在海边拥挤的帐篷里。每天清晨他排队接取饮用水和洗漱用水,用柴火煮茶,往面包上撒香料——用能找到的任何东西抵御饥饿。
其余时间他在营地游荡。失学已逾两年。“没人叫我读书,”他说,“如果有学校,我立刻就去。”双亲皆已遇难,他成为战争制造的数万名孤儿之一。
冲突彻底剥夺了孩子们的正常童年。他们或伤或亡,失去至亲,忍受长期匮乏。
“这种极端环境将严重阻碍心理、人格与身体恢复。”巴勒斯坦孤儿救助组织总干事塔里克·艾姆泰拉指出。西岸巴勒斯坦统计局四月数据显示,超3.9万名儿童至少失去一位亲人,其中约1.7万名成为双亲尽失的孤儿。
沙赫马居住的难民营收容了超4000名失亲儿童,另有1.5万人依靠营地获取食物医疗等服务。营地负责人表示,许多孩子频做噩梦或焦虑不安,部分因经历极端创伤而失语。
即便家庭完整的孩子也面临教育系统崩塌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数据显示,超70万儿童失学,几乎所有校舍需修复重建。所有大学均告关闭,多所被以军炸毁——指控哈马斯在校内活动。
流离失所者营地涌现临时学校,孩子们聚在防水布下,席地而坐。文化艺术组织“玛雅森”在南部开设教授阿语、英语、数学与科学的课堂。
8岁的拉蒂尔·纳贾尔说重返课堂令她欣喜,但学校缺少桌椅、蜡笔和纸笔。热爱数学的她立志成为建筑师——像那位战死的叔叔一样。
机构负责人纳吉拉·阿布·纳赫拉表示,教学重点不在学业成绩,而是通过趣味活动、运动与音乐守护心理健康。下课铃响时,孩子们总不愿回到排队领水取食的现实。“在这里,”她说,“他们才能短暂做回孩子。”
破碎的经济
战前,莫娜·加拉伊尼是罕有跻身加沙商界精英的女性。她合伙经营超市,独资管理“大口咬”餐厅与滨海高档“根源酒店”。
如今她的商业版图所剩无几。“超市?烧抢一空。”冲突初期逃至埃及的她通过电话说。“餐厅?不复存在。”“酒店?需要彻底重建。”
去年她在开罗开设巴勒斯坦餐厅“根源”,虽渴望重返加沙,但强调那里必须恢复稳定、水电供应——“生活的必备要素”。然而归期无望。“一切重建都缺乏清晰蓝图,”55岁的她说,“所有人的未来都迷雾重重。”
战前加沙因以色列与埃及部分封锁已贫困交加,但仍有商人投资商场、餐厅、工厂与农场,维系着当地就业与粮食供应。
战争几乎冻结所有正式经济活动,世行数据显示失业率至少80%。联合国报告超70%灌溉井、温室与渔船损毁,七月时完好且可耕作的农田不足2%。
世行定义的“多维贫困”人口比例——即缺乏收入、教育及水电等基本服务——将从战前64%飙升至98%。
无数创业者资产尽毁。61岁的哈桑·谢哈达曾雇佣200余名工人生产销往以色列的牛仔裤与外套。战争摧毁了配备60台缝纫机的车间,举家南逃时携带的20台设备也因电力短缺难以运转。
他既无法工作也不能归乡,只能不断确认前雇员们的死讯。但他仍期盼和平降临,期盼双方认清命运相连:“以色列不能放弃我们,我们也不能放弃以色列。若没有坚实根基的和平,一切终将徒劳。”
本文原载于《纽约时报》
作者:本·哈伯德、比拉勒·什巴伊尔、伊亚德·阿布赫维拉
摄影:萨赫尔·阿尔戈拉、迭戈·伊巴拉·桑切斯
©2025 纽约时报公司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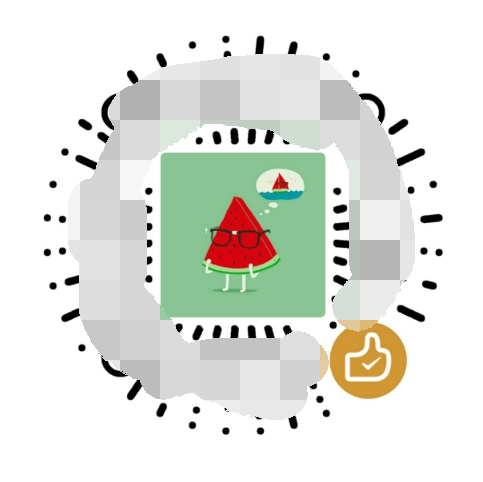
暂无评论
发表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