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芝加哥电 — 在近日一次视频通话中,芭哈拉的面容在屏幕上忽明忽暗——昏暗中她锋利的颧骨几乎难以辨认。喀布尔又停电了。
这位19岁少女与伊利诺伊州的家人通话仅几分钟,屏幕就陷入漆黑,诡异的寂静笼罩了整个房间。
这个七口之家已经四年未能团聚,他们最小的女儿至今音信渺茫。在相距半个地球的客厅里,家人反复咀嚼着与她的别离。
"我们每时每刻都活在煎熬中,"父亲蜷缩在地板上泣不成声,"脑海里全是她的模样。"为安全起见,本报道隐去芭哈拉父母姓名。
2021年8月,美军撤离阿富汗后塔利班兵临城下,芭哈拉一家随着数千逃难人群涌向机场。
芭哈拉的父亲曾为美军担任安保人员近二十载,此刻最恐惧新政权的清算。夫妇俩从未想过背井离乡,但儿子曾被塔利班枪击腿部的遭遇,迫使他们必须为家人寻找生路。
然而机场突发闪光弹爆炸,母亲面部重伤血流如注,15岁的瘦弱少女芭哈拉在混乱中被冲散。
父亲试图折返爆炸现场寻找女儿,却被美军士兵拦下,对方承诺会找到她让全家团聚。
年长三岁的姐姐塞塔拉在恐慌中丢失了鞋履,赤脚挤在满载数百人的运输机上,竟浑然不觉脚底冰凉。对母亲伤势和妹妹下落的担忧吞噬了她。
在转机德国的记忆碎片里,塞塔拉依稀记得有人递来一双旧鞋。
破碎的拼图
其余家人通过"盟军欢迎行动"抵美,该计划在塔利班接管后安置了逾8.8万阿富汗人。
这个家庭的分离并未止于芭哈拉。长子被安置在华盛顿,虽已成家立业,但在这个脆弱时期,距离仍是切肤之痛——母亲至今未曾拥抱自己的孙辈。
其余五人在新泽西军营滞留半年后迁往伊利诺伊——据说那里有庞大的移民社区。他们在郊区旅馆又度过数月,最终落户芝加哥外一条绿树成荫的静谧街道。
芭哈拉的移民进程因多重原因停滞:不熟悉申请流程,机场爆炸中丢失所有证件。但在拜登任内仍在缓慢推进。
直到特朗普政府上台后,她的案件进展彻底陷入僵局。
22岁的塞塔拉在家庭悲恸中扛起重担:陪母亲做康复治疗、烹饪、在快餐店打工。
她在电话里向妹妹描述美国的新生活——诸如深夜散步的微小自由。但负罪感如影随形,将她困在公寓,远离校园与朋友。
"总忍不住想"如果芭哈拉在,她该多喜欢这些","塞塔拉说,"所有一切。"
没有妹妹的圆满令人怅然,她宁愿独守空房。
喀布尔频繁停电与塞塔拉紧凑的日程,让姐妹通讯难上加难。每次连通时,她们总沉浸于共同度过的十五年往昔。
塞塔拉曾通过视频向妹妹展示附近的公园和密歇根湖岸。
"我告诉她终有一天会来到这里,"她说,"哪怕要等五年,十年。"
塔利班阴影下的日常
自202年掌权以来,塔利班通过法令统治阿富汗,废除民主制度,代之以严苛的伊斯兰教法。
当权者禁止六年级以上女童入学,将女性驱逐出公共领域,剥夺司法保护。
芭哈拉借宿在邻居家,靠家人汇款支付费用。她多数时间独居一室,甚至不被允许共进餐食。
电力时断时续,净水难寻。她几乎足不出户。
据家人所述,少女若无男性监护人陪伴,连咖啡馆和餐厅都不得入内。塔利班不时逐户搜查特定女性,尤其针对曾为前政府或国际组织工作的人员。
芭哈拉常听闻女性离奇失踪的新闻,家人往往求告无门。
"若是儿子滞留,或许我们还不至于如此绝望,"64岁的父亲哽咽道,"可她是我最美丽的小女儿啊。"
阻断的归途
志愿者迪塔表示,芭哈拉的家庭只是美军撤离后数千个受困家庭的缩影。
由于鲜有机构接手新案件,迪塔创立了支持阿富汗家庭的非营利组织"罗娅",尤其关注曾服务美军的家庭。她与塞塔拉父女情谊深厚,持续跟进他们的移民进程。
2022年2月入住旅馆后,芭哈拉一家面对堆积如山的文书工作。作为申请人的父亲既不识字,又因严重心理创伤屡次错过电话信件。
"她的缺席让我们都在心理上备受煎熬,"父亲说,"这本不该是我们的命运。"
在当地机构和志愿律师协助下,他们于2022年8月申请庇护,历时一年终获批准。随后提交的团聚申请却因文件收集——尤其是耗时数月才取得的芭哈拉护照——再度延迟。
2024年4月护照到位成为关键转折,案件得以移交美国国务院及阿富汗撤离协调办公室。
虽然协调办确认收到材料,但随后音讯全无。2024年大选后,家庭的希望愈发渺茫。
3月咨询后续进展时,芭哈拉收到联邦政府通知:"难民旅行与安置处理暂停,重启时间待定。"
5月政府宣布关闭协调办,芭哈拉与无数案件面临永久搁置。她发邮件追问解释。
"即便值得优先处理的案件也无法加速,出于行动安全无法提供时间表,"协调办旅行处在7月11日邮件中回复。
国务院未就芭哈拉案件或现有安置方案予以置评。
迪塔补充,语言障碍使芭哈拉与联邦机构沟通举步维艰。
"所有通讯、文书没有母语支持,"她叹息道。
多数阿富汗撤离者持人道主义假释身份入境,这种临时身份无法转为合法居留或实现家庭团聚。
2022年提出的《阿富汗调整法案》本可提供永久居留权并建立团聚机制,但该法案三度在国会搁浅。
2025年的春天
芭哈拉在达利语中意为"春天",象征新生。但对这个家庭而言,希望比任何时候都更遥远。记忆中在开斋节相聚于杏树下的村庄,恍如隔世。
得知安置进程中止后,芭哈拉将处境归咎于家人。她彻底断绝联系,甚至拉黑了母亲和姐姐。
"她哭着说我欺骗她,愚弄她,"父亲痛心道。塞塔拉一言蔽之:"我们逃出来了,而她被困住了。"
塞塔拉明白邻居的照拂与亲情不可同日而语。分别前芭哈拉仍黏着母亲,有时还会钻进母亲被窝,最爱喝她做的酸奶油阿富汗面汤。
如今芭哈拉靠打扫房间消磨时光,常因无事可做以泪洗面。
塞塔拉正备考GED期望进入社区大学,但妹妹近期的沉默让她难以专注。
她欢忆起在美国校园第一次跃入泳池的瞬间——这在家乡永远无法实现。水流暂时冲散了乡愁与恐惧,她甚至骄傲地提及某次未穿救生衣的纵身一跃。
她渴望与妹妹共创自由的新记忆,而非沉湎往事。夜深人静时,她总在脑海中预演重逢后的第一个场景。
她说最想并肩骑着单车穿越社区——这是她们曾经幻想却不敢奢望的平常幸福。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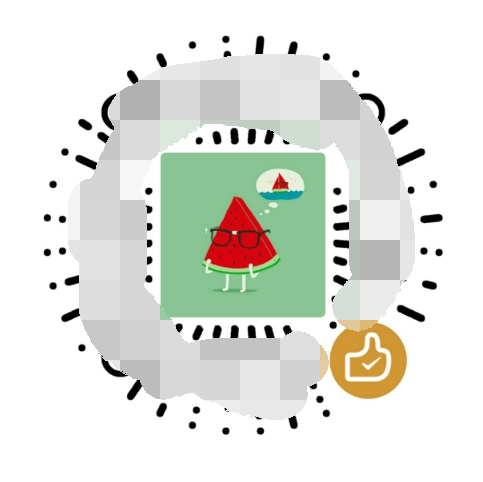
暂无评论
发表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