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早在1930年,约翰·梅纳德·凯恩斯就预言:到2030年,他这一代的孙辈(大致就是我们这代人)将达到消费饱和点,因此工作时间将大幅减少。
这位20世纪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在《我们孙辈的经济前景》中预测,"进步国家"(泛指欧美地区)的生活水平将提高4到8倍,平均每周工作时间将缩短至仅15小时,或每天轮班3小时共5天。
本质上我们将回归幼儿园作息——上午9:15到12:15工作,上午茶歇来点三角奶酪和葡萄。简直是天堂。
讽刺的是,全球唯一实现这种工作生活境界的,竟是石油富国的阿拉伯人。据说依靠石油收益生活的阿联酋、卡塔尔和科威特民众,日均工作时间仅三四个小时。
然而对大多数打工人而言,每周平均工作时长与凯恩斯时代几乎无异。
回看历史,凯恩斯对社会和人类行为的预判存在多处偏差。
他预言生产将全面机器人化,人类得以减少工作;还认为随着财富增长和基本需求满足,人类会"理性"选择减少工作。
两项预测全盘皆输。凯恩斯以英国绅士阶层为参照——那些持有土地、房产和金融资产的爱德华时代精英。当资产增值时,他们收入增加且明显减少工作。
但现代人对工作的执着早已超越金钱报酬,涵盖了地位、社交关系和个人成就等复杂因素。
我们的消费习惯也远超基本需求。人们越有钱就越想要——豪华轿车、最新科技、爱马仕铂金包。与技术发展会抑制消费的预测相反,科技反而助长了消费主义。
就在我撰写本文时,已经三次起身签收亚马逊的包裹。
美国——这个主导过去100年人类历史的经济文化体——或许最有力地驳斥了凯恩斯"财富增长带来闲暇增多"的核心假设。
哈佛经济学家理查德·弗里曼指出:美国人均GDP比法德高出30-40%,但美国工作者工时比欧洲人多30%,休假更少。
"凯恩斯孙辈选择拼命工作,标志着工时与薪酬历史性反比关系的逆转。"弗里曼写道,"过去几十年,穷人比富人工作更久。他们必须辛苦劳作养家糊口。不工作就饿死。"
"富人凭借土地资产或世袭地位,大可随心所欲地悠闲。"有闲阶级"这个词曾具有真实含义。"
"但在20世纪下半叶,时薪与工时的反比关系发生逆转,至少在美国如此。"他说,"工作狂富人取代了有闲富人。高收入者比低收入者工作时间更长。"
当然,不仅是美国工作狂证伪了凯恩斯预言。
很多时候,标准的40小时工作周甚至无法覆盖房租水电和日常开销,因此多数人根本不敢减少工时。如今多数家庭还必须依靠双份收入才能运转。
这就要提到财政部最新发布的疫情后爱尔兰劳动力市场报告:当地工作者周均工时比疫情前减少两小时。
该趋势部分与远程办公普及相关。
这一发现引爆了当下劳资双方关于混合办公的拉锯战——究竟是助长了摸鱼和低效(某些CEO观点),还是代表了让员工更幸福、特别是促进女性就业的宝贵工作模式变革。
但报告显示工时下降几乎涉及所有行业——包括需要现场作业的领域——表明灵活办公并非"主要驱动因素"。
值得注意的是,富裕欧洲国家的人均工时确实会随财富增长而下降。
当然也存在另一种可能:这些基于员工自述的数据(疫情后可靠性莫名下降)只是统计噪声,我们实际并未减少工作。其他调查显示平均工时并无变化。
但若我们工时真的与前辈相当甚至更少,为何人人都感觉被掏空?
或许人均工时指标掩盖了真正的元凶:家庭总工时、通勤时间延长、亲力亲为的育儿模式、以及"永不下线"的工作文化。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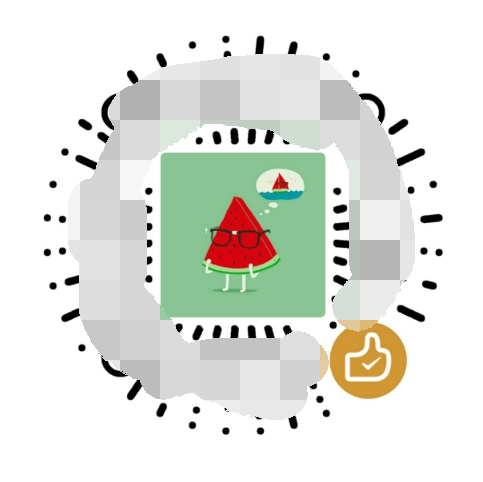
暂无评论
发表评论